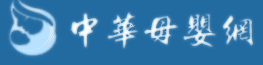偏偏潘金莲不认命,偏偏这时武松出现了,而武松这个充满男人气息的人物的出现,彻底唤醒了潘金莲身体最本能的渴望……潘金莲同志可能当初是想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只可惜她虽然使尽浑身解数,武松这个认死理的家伙就是不领风情!
但这欲望的火苗一旦点燃,要想扑灭谈何容易。偏巧这时潘金莲同志失手将支窗户的木叉跌落在了风流公子西门庆的身上,而偏偏潘金莲同志的美貌与风情正合了西门庆的胃口,又偏偏生出那么个多事的王婆,又偏偏潘金莲同志心灵手巧会一手好针线活。这么一来,天时地利人和,潘金莲便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露,或者说是干柴遇到烈火,一点就噼哩叭啦地烧了起来。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施耐庵这老先生,是存了心把潘金莲往死路上写啊。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潘金莲渴望正常的生理满足,是一个女性应有的权利。如果放在今天,她可以离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只不过她错生在施耐庵笔下的年代,在那个“通奸死罪”的程朱伦理统率天下的时候,她要活下来,就该认命。但潘金莲偏偏奢求得到起码的性满足(红杏出墙就罢了吧,武大郎其实也不会拿她怎么样),并欲盖弥彰,听信怂恿,亲手逼武大郎喝下砒霜,最终铸成大罪。
至此,一个以典型的良家妇女形象出场的弱女子,随着事态的发展,在经历了内心世界充满矛盾的斗争并步步转变后,从一个值得同情的弱女子转变成了可怕的刽子手。
潘金莲的情欲世界
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性革命”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过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说来,“性过度”的女人有两大类,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虚拟的性高潮”者,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但旺盛的性欲(原我)与薄弱的道德意识(超我)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实质的性高潮”者,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她更是一个“生性淫荡”的女人。作者借相术来显露她这种本性:在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说她“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潘金莲之所以对“性”特别有兴趣,乃是因“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与她的“童年经验”无涉,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存在,颇堪怀疑,也值得讨论。
(责任编辑:陆彩虹)